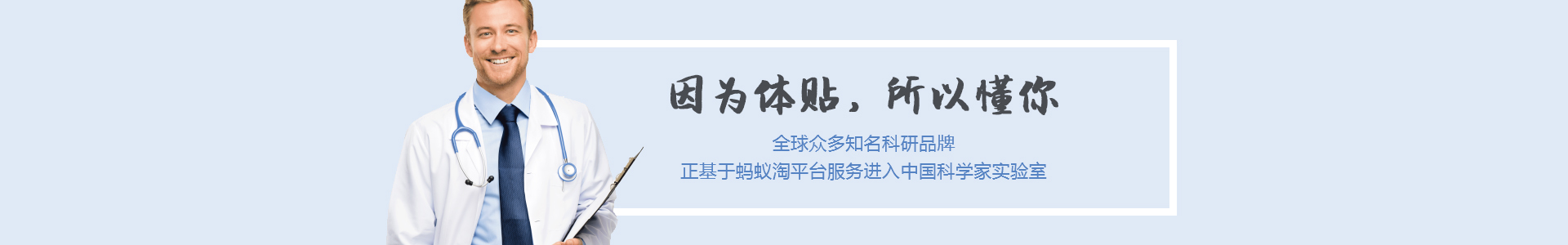导语:Incel是在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里”,被划定为“loser”的一个群体。他们中绝大多数为白人男性,认为自己不受女性青睐的原因是女性只喜欢长得好看的男性,只为那些男性提供“性资源”。他们憎恶女性,更憎恶自己“得不到”她们的现实,于是开始探讨如何以暴力行为“毁灭”。面对巨大的社会机器,没有资源的个人渺小如沙粒,被划定为失败者的Incel们充满怒火。
5月的某一天,美国德克萨斯州圣达菲高中,一名17岁的少年举枪射击,杀死了10名师生。
枪击者并非一时冲动,他做过杀人及自杀计划,四月底还在脸书上传过一张印有“天降杀者”(Born to Kill)的T恤的图片。5月10号左右,他再次向喜欢已久的女孩告白,被女孩当着众人的面拒绝。5月18号,有目击者称,枪手冲进教室大喊“Surprise!”然后向教室中的人群开火,女孩在受害者之列。在法庭上,枪击者对警察说他是以自己不喜欢的学生们为目标的。
这并非孤立。一个月前,加拿大多伦多,一位25岁的男子在北约克中心商圈开车乱撞,致10人死亡。此前他在脸书上呐喊:“Incel(非自愿独身者,也有翻译为非自愿处男)要反叛了!我们将推翻所有Chads(受欢迎的男性)与 Stacys(受欢迎的女性)!向埃利奥特·罗杰绅士致敬!”
而他所说的埃利奥特·罗杰,于2014年3月份,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附近开枪,致6人死、14人受伤,随后自尽。他在之前上传YouTube的视频中说,他这么做,是为了惩罚那些拒绝他的女性,以及总能吸引到女性的那些男性。
这几个案件看似有些联结之处,但他们并不能用一个孤独的少年遭遇欺辱与拒绝,以极端方式报复相关者及无辜者的方式讲述。他们将“非自愿处男”这个群体及其背后的问题凸显出来,是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下”(贝尔·胡克斯语),一些白人男性“loser”们,在对自己及体制绝望的困境下,以仇恨女性整体、伤害不幸女性(及男性)个体的方式,寻求出口的做法。
而这里的问题是,在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下”,为什么白人男性“loser”会将愤怒转向女性整体呢?为什么是具体女性要为男性“loser”的失败付出沉重代价?
Incel是involuntary(非自愿)与 celibacy(独身者)的合成词。人们普遍认为该词应归功于加拿大人Alana,她在1993年创立了Alana’s Involuntary Celibacy Project,该项目是一个在线空间,鼓励较晚才有性经验的人们自我表达。不过,出乎初创者意料的是,Incel后续发展成了一群“loser”最后的据点,网上的一群厌女团体常常用这个短语代指自己。
他们中绝大多数为白人男性,聚集起来的最直接原因从女性那里“得不到”“性资源”,或者感受到“性挫折”。他们认为自己不受女性青睐,是因为女性只喜欢长得好看的男性,只为那些男性提供“性资源”。因此他们憎恶女性“随意使用”她们的身体,更憎恶自己“上不到”她们的现实。于是开始探讨如何以强奸等暴力行为“拿”到女性的身体。
渴望与憎恶共在的结果是一种极端的想法与行为,即干掉Stacys(受欢迎的女性),也干掉Nomines(普通的人)。这些Nomines外表不出众,居然能拥有温暖的爱情,他们也接受不了。如此算下来,只有干掉了所有女性,他们才舒服。
Incel们羞于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,在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里”,作为白人男性的他们,却成为了“loser”。但是,这是一种缄默的承认:谁都知道,但谁都不说出来。就算是有人说,那也仅限于自嘲,如果外人用“loser”描写他们,那基本等于踩了地雷。
他们选择集体回避一些外在的现实,把“loser”的不幸现实归咎于自身——生来外貌寒碜,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撑,也没能实现理想的教育水平……因此,这是自身的失败,是一件丢人的事。然而他们选择性忽视的是,这种境地或许是是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”运作的必然结果。白人至上主义者坚信,有色人种的贫困,是他们懒惰、愚蠢的结果。在他们眼中,鼓励竞争精神的社会体系为个体的奋斗提供了相当好的环境,个体若失败了,那就是自己的问题。这一信念蔓延开来,便是要求个体为自己的贫困负责,到了白人男性这里也不例外。
不过,资本主义天生具有支配性与剥削性,占有生产手段的人,控制着劳动力也控制着市场。资源只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,绝大部分个体的一生都只作为劳动工具出现,一旦一个人的“工具性”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要求,这个人就会被抛离出资本主义体系。面对巨大的社会机器,没有资源的个人渺小如沙粒,例如在这个体系下被认为是“loser”的“Incel”们。
同样,父权制的阴暗之处在于,它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理念。相信男人是要来统治、引领人类的,女人是要服从并服务。一旦这种规则被打破,父权制的遵从者们就会无所适从,变得躁动不安,因为一些“自然的”东西“不自然”了。
无论是白人至上主义,还是资本主义,还是父权体系,它们共享的基石是不断地制造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(白人与其它种族;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;男人与女人),不断地确立中心与边缘(白人中心-其它种族边缘;资产阶级中心-工人阶级边缘;男人中心-女人边缘),并时不时地抛弃一些不合格者(不能胜任中心位置的白人男性,典型如Incel)。
因此,作为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”的必然产物,Incel们处于极度的矛盾与撕裂中:在白人至上与父权体系下,他们是支配者,本应该享受当前世界体系带给他们的优渥资源;然而,因为不能占据资本主义内的支配位置(毋宁说是被资本主义抛离),他们发现自己既受其他种族的威胁,又无力握住对女性的“天然支配权”。
他们烦躁、充满怒火。
与略显抽象的种族威胁相比,无力接近女性“性资源”对Incel来说显得更为致命,这直接关系到他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在Incel社群内,最核心的讨论对象是女人,讨论范围极广,从如何“上到”女人,到如何伤害女人。随便打开一个Incel聚集的网站,如Incels.Me,就会看到女性的卡通性感图片、去哪里找女人的问询,以及对加拿大卡车撞人事件的讨论。绝大多数帖子支持撞人者,还有人表示,这只是“Beta uprising” 的开始。Beta uprising约等于Incel rebellion,指得不到爱的男人报复女人的集体行为。
而这正是Incel群体最需要被警惕之处。个体对女性的仇视,在抱团后成为了一场旨在伤害女性的集体运动,成为了又一种现代恐怖主义。他们的反女性主义、厌女症、种族歧视、对暴力的拥抱,让他们得到了另类右翼(Alt-right)这把政治大伞的“庇护”。
另类右翼的说法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·史宾赛(Richard Bertrand Spencer)在2010年左右初创,它强调白人身份的优越性,旨在维护白人利益。汇集在这把大伞下的,有白人至上主义者、新纳粹主义者、新法西斯主义者、种族主义者、反女性主义者、厌女症患者、恐同者、恐伊斯兰主义者……总而言之,他们走出了合理意义上的右翼范围,是极端右翼。
而Incel们则是另类右翼这个极端中的极端存在。如果说“得不到”女人让他们聚集成群,那“干掉女人”的目标,则让这个团体变得稳固结实,而另类右翼的标签,让他们带有了“政治运动”、“改变世界”的荣誉感。不过这里的改变世界,却更有着“如果改变不了世界,那就毁灭它吧”的虚无意味。
在2017年出版的《杀死所有普通人》(Kill All Normies)一书中,左翼学者Angela Nagle用尼采的虚无主义来分析Incel——假如有了“性资源”与金钱,他们能立即投入消费的狂欢中,瞬间忘记厌世与虚无。Incel的这种因匮乏而产生的虚无意味,恐怕连另类右翼的中坚派都会心生戒惧。
因为两手空空,大脑也干枯,Incel们没办法拿出更好的政治资源为另类右翼效力,只能把另类右翼的主张推向更极端,以证明他们更“先进”,更“内行”,一如《权力的游戏》中的小剥皮。只有把哪怕连自己都憎恨、恐惧的东西,转变成手中的利剑时,他们才能找到一点存在感。这把利剑就是憎恶与伤害更弱的群体,尤其他们“得不到”的女人。
Incel们并不勇敢,相反,他们很懦弱。他们是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”下自动产生的”loser”与冗余,是竞争体系下的牺牲品,是胜利者那里必要的炮灰。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一点。稍微看看身边的左翼青年,或者听听左翼的声音,就知道自己该责怪、痛恨的是当前的体系。然而他们太懦弱了,没有勇气这样做。
因为左翼的主张,会让他们失去这个等级体系。而这个等级体系,即使让他们总以垃圾的形式呈现,也给他们的人生兜了底——他们是白人、男性。虽然在最底层,但却在支配者的最底层。所以,就算是痛恨这个体系,痛恨中更有的是敬畏与向往。正如小剥皮,就算他是私生子,也是领主的儿子,比村子里的孩子不知道强多少倍了。Incel们站在等级体系里往下看,还有庞大的人群,被牢牢钉在被支配的位置上,如其他种族的人,如女性。
那如何保住这个天然优势?尴尬还是那个尴尬,他们毫无有效的政治资源,唯一能做的,就是一再手动重现“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”的基石——生产与再生产他者,制造对立,欺压弱者。在具体表现上,则是毫不掩饰地听从力比多的指挥,仇视、报复女性,意淫对女性的暴力,渴望女性表演服从与听话。
不过,Incel与女性之间的关系,绝对不是渴望与被渴望,仇恨与被仇恨那么简单。Incel们对女人的强行想象,与他们的实际行为互相印叠,构成了一出滑稽剧。
一方面,作为群体的女性,的确在被支配的位置,哪怕星光闪耀的好莱坞大牌女性,都得用小心谨慎来保全自身。小说、电影、游戏以及他人的口中,的确充斥着简单幼稚肤浅的女人。可另一方面,强大的女人似乎太多了。这些女人既能处理好自己的事,还能影响到周围的人。不说遥远的谢丽尔·桑德伯格,就是他们上高中时的同班女生,也强大到让他们不敢直视。
父权制豢养下的Incel是凌乱的。他们一心想把女性简化为与性相关的物品或工具,把女人定格为感情用事、易冲动、爱抱怨、歇斯底里的动物,也希望女性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般头脑简单。可这种自我欺骗总是遭到现实的暴击。
一种无法遏制的恐惧在Incel们中间蔓延,他们羸弱的支配性地位,要么遭遇女性的围攻,要么遭遇女性的无视。这种恐惧,撞击出了此前他们精心掩藏的另一种更大的恐惧,即他们自身男性气质的缺失。
之所以强调女人是歇斯底里的情感动物,之所以嘲笑男同性恋,就是因为他们是“统治阶级”内的弱者、“娘炮”、“女人”。可能是太急于甩掉这些头衔,他们采用自己所宣称的最鄙视的方式:最冲动、最感情用事、最歇斯底里的极端报复行为。他们亲自上演一出又一出这样的荒诞剧,把最懦弱的宣泄自欺式地解读成英雄的壮举。
生理性别女的女性主义者,恐怕是Incel所有痛恨的群体中最痛恨的一类。在他们眼中,这些女性主义者颠乱了父权主义纲常,鼓励女性与男性作对并争夺男人的地盘,自己落到今天这般下场,女性主义者功不可没。
然而他们不知道,或者不想承认的是,女性主义者,尤其左翼女性主义者,正是能真正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人。这些女性主义的目标,是从根本上推翻白人至上主义、资本主义与父权体系,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个人平等与自由的社会。那样的社会,会帮助每一个有差别的个体发展自身的潜力,“loser”这样的概念恐怕都会消失。
可惜的是,目前看来,这些“loser”还是会以消灭女性为傲。找不到自我的那种焦躁感,让他们不愿放眼去看遥远的将来。当然了,他们身处的这种社会体制,也没给他们留找到自我的足够空间。
参考文献:
Bell Hooks. Feminist Theories: From Margin to Center. London. Pluto Press, 2000.
Nagle Angela. Kill All Normies. Zero Books, 2017.
Williams, Zoe, “ ‘Raw hatred’: why the ‘incel’ movement targets and terrorises women,” The Guardian, 25 Apr 2018,
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world/2018/apr/25/raw-hatred-why-incel-movement-targets-terrorises-women?CMP=Share_iOSApp_Other#img-1
Turkewitz, Julie & Bidgood Jess, “Who Is Dimitrios Pagourtzis, the Texas Shooting Suspect?” The New York Times, 18 May 2018,
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18/05/18/us/dimitrios-pagourtzis-gunman-texas-shooting.html
Duke, Alan, “Five revelations from the ‘twisted world’ of a ‘kissless virgin’”, CNN, 28 May 2014,
https://edition.cnn.com/2014/05/25/justice/california-shooting-revelations/index.html
本文链接: http://richardbertrand.immuno-online.com/view-749160.html